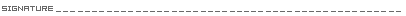茨威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,塑造了一个为爱默默奉献的年轻女子的经典形象。她不求回报、毫无妒忌,十几年如一日地爱着一个作家、一个风流放荡的作家。
曾经很惊讶,如此女性化的作品,怎么会出自一个男作家。斯蒂芬·茨威格就是有这样的天赋,敏感细腻既是他的长处,也是他的短处。最终,他和妻子在寓所一起服毒自杀,也是由于———“我精神上的故乡已毁灭,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我的生活了。”
徐静蕾的同名电影上映之后,有网友对原作者茨威格先生很是不满,认为他宣扬大男子主义。这实在是误读了茨威格。他正是以笔下这个用一生来实践爱情的女子,批判了那些醉生梦死、只有肉欲没有情感的污浊男人。
很喜欢徐静蕾执导的《来信》,虽然没有明显强烈的戏剧冲突,但她的叙述节奏可以称许为流畅。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,都不会觉得影片有沉闷之嫌。她也是一个成功的编剧,“移花接木”的活干得蛮漂亮。
毛泽东说过,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。男同志能做到的,女同志也能做到。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,这句话也许可以这样说:“时代再不同,男女都不一样。女同志能做到的,男同志不一定能做到。”像勃拉姆斯和金岳霖那样的痴情男儿,不能说绝无仅有,也是凤毛麟角。
男人若是爱上一个女子,对她最高的尊重就是娶她为妻。万一求爱不得,他会说:“大丈夫何患无妻!”倘若抱得美人归,那当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,很快就会变成“蚊子血”和“饭粘子”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佳话,不能说绝无仅有,也是凤毛麟角。
有人骂毕加索滥情,至少他在与某个异性相处的那几个月里还能专情。不像《来信》中的这个作家,换女人如同换一次性筷子。
时代的年轮无论增长多少圈,有的女人对爱情的痴心和执着都不会改变。只不过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,都会遵循世俗的轨道,在生活的磨盘下把心磨砺得日益粗糙。像《来信》中的女子这样把毕生交付给心上人的,不能说绝无仅有,也是凤毛麟角。
近日,英国《自然》杂志首次公布了人类性染色体—————X染色体的基因序列草图。科学家发现,女性的性染色体上的基因有一小部分积极活跃,由此导致女性在心理和性格上不同于男性。也许,就是它们,令有的女性痴心不改终生不悔地为爱付出吧。
爱,确实是有男女之别的。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05-4-22 16:09:24 [显示全部帖子]
Post By:2005-4-22 16:09:24 [显示全部帖子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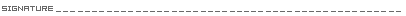

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05-4-22 23:42:50 [显示全部帖子]
Post By:2005-4-22 23:42:50 [显示全部帖子]